返本开新,贯通中西: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商学教育探索
杨海锋
【摘要】当代中国大学的商学院里,西方的理论几乎一统天下,这既可喜又可悲。如何在实践中和理论上将西方现代的商业模式和中国本土的传统文化融合起来,并在我们日常的课程教学中切实地体现出来,已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作者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在经管课程的教学中整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因素,本文即是关于此一探索的一些思考。
【关键词】中国 传统文化 商学教育
【收稿日期】
【作者简介】杨海锋,男,1977年7月生,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商学分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等。
在当代中国大学商学院的课堂上所传授的,几乎都是清一色的西方原创的理论,这既是一件可喜的事情,也是一件可悲的事情。可喜的是,这是中国社会日益开放以及中国经济日益发展的表征,如今西方的经济、管理领域的理论几乎可以做到同步引进。可悲的是,虽然我们与西方尾随得越来越紧了,但始终未能与中国本土的文化完成深层次的整合,也正是因为没有完成深层次的整合,我们始终无法在自己的文化土壤中生长自己的理论。这一点,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都应该有切身的体会,在我们使用的商学教科书中,既很少看到对中国古代经济、管理思想的用心整理和实质性发展(即使有,也是很突兀的加入一节),更看不到中国近现代有原创意义的观点(即使有,也不见重视,如鞍钢宪法)。或许,可用晚清学人邓实的一句话来形容目前商学领域——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如神圣。这无论如何是与中国这样一个曾为世界贡献过无数原创思想的泱泱大国不相称的。
正是基于这一想法,作者多年来在自己讲授的管理学、经济学课程中尝试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的因素,后来又专门开设了名为《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的专业选修课以及名为《从内圣到外王》的公共选修课,希望能在此方面做一些尝试和探索,虽然势单力薄,但还是得到了不少学生的认同和欢迎。本文限于篇幅,只谈谈与此相关的两个问题。
传统文化对现代商学:阻力还是助力?
长久以来,主流的观点一直认为,我们当务之急是如何跟上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学、管理学理论前沿,中国传统的那些东西早该扫进历史垃圾堆里去了,而且这些“封建残余”、“民族劣根”扫得越干净,越有利于西方先进经验的引进,越有利于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这种观点不但现实中被多数人认可,而且有理论上似乎也有根据。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有一个著名论断:新教伦理促进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儒家伦理却阻碍了东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这就是所谓的“韦伯命题”。韦伯认为这不仅仅是中国社会结构的原因,而主要是蕴含在中国传统宗教中的精神气质。
但是,20世纪70年代日本经济的崛起,以及随后亚洲四小龙经济的腾飞,引起了许多学者对韦伯命题的反思,他们认为儒家伦理不但不是阻碍经济的因素,反而有促进经济的作用。甚至有学者认为,新儒家文化与韦伯阐述的清教伦理相比更具有优势(称为“反韦伯命题”)。
其实“韦伯命题”与“反韦伯命题”并不存在本质的矛盾,作者曾在《儒家文化对家族企业的影响:阻力还是动力?》一文中,尝试将这两个命题在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统一起来。在宏观层面,儒家文化对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作用并不一样。在儒家伦理之下西方式资本主义不容易自发产生,这的确是事实;但在儒家伦理之下完全可以很好地发展西方式资本主义,这同样是事实。在微观层面,儒家文化对家族企业的不同时期,影响也不相同。比如儒家的小传统有利于中国民营企业的一次创业,但不利于其“二次创业”;而儒家的大传统恰恰有助于突破二次创业的瓶颈。总而言之,我们不能笼统地说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对西方式的资本主义是促进还是阻碍,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其间充满着大量对立而又统一的东西。重要的不是囫囵吞枣地肯定或者否定它的作用,而是更好地理解它、体悟它、挖掘它和发展它,以发现它的价值。
事实上,儒家文化对现代商业文明的正面价值,早在东西方明碰撞的初期,就已有事实上的明证。比如日本明治维新时代著名的实业家涩泽荣一(1840—1931),就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进行了成功的探索,他一生创办了500多家企业,遍布银行、保险、矿山、铁路、机械、印刷、纺织、酿酒、化工等日本当时最重要的产业部门,被人称为“日本现代企业”。与此同时,他成功地将“《论语》”和“算盘”结合在一起,提出了“义利合一”、“士魂商才”等思想。作者曾看到有中国现代儒商之称的李嘉诚对长江商学院有一段寄语:“传统的儒家思想推崇道德标准的作用,而今天很多商业管理课程则强调效益和盈利是衡量企业成功与否的主要标准,这两种有着明显冲突和矛盾的取向都是不完整的,最重要是寻求两者圆满的融合。”这与涩泽荣一的思想也是不谋而合的。
就现实而言,目前我们的整合还流于表面,无论对西方的商学理论还是中国的传统文化,都未能深入其根源。任何一种有效的方法、模式,其背后必然连带着这种方法、模式得以产生发展的精神背景(用中国文化的语言说,就是“术”之上的“道”),脱离了这个精神背景,这种方法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所以,如果我们不能在深层的文化根基中接上西方文化的源头,实现两者的整合和贯通,西方的模式、方法就很难真正有效地“嫁接”进来,即使“嫁接‘进来了,也是徒有其形,不得其神(参见图1)。因此,作者在教学中特别强调沉下心来阅读“元典”(包括东方的元典和西方的元典),深入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深层,因为只有深层实现贯通,表层的建构才有可能。为此,作者在还在课外专门组织了“经典会读”活动,作为课程的辅助,在关于经典的阅读和对话中真正贴近东西方的文化之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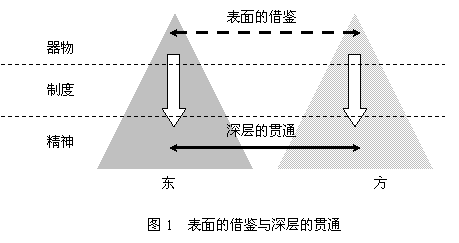
当代中国的商学教育:方法缺失还是精神迷失?
作者在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经常发现不少学生乃至老师将“假设”当作“事实”,把经济人的假设——每个经济主体都在现有约束条件下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或者通俗的说,人都是自利的)——奉为至理,认为经济的发展的原动力是资本家无限贪婪的欲望,中国社会过去不承认人的自利性,不承认人性本恶,从而压制人的欲望,所以市场经济发展不起来(且不论中国历史上的市场经济是否真的没有发展)。
事实上,只要我们仔细想一想,就会发现,较少约束的贪婪欲望并不必然带来经济的繁荣,也可能带来混乱和破坏。古今中外,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在那些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时期,人的恶性发挥得淋漓尽致,但显然没有社会经济的繁荣。其实任何外因必须通过内因起作用的,这是很清楚的道理,自由、宽容的环境是必要的,但只是外因,重要的是内在有没有一种能将人们释放出来的欲望引向一个建设性方面的精神。在西方,马克斯·韦伯早就看到了这一点,他认为具有勤勉,节俭,虔诚,敬业等等优秀品质的新教伦理,孕育了资本主义精神,促成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或许是因为长久以来对“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等观念的误解,使得我们把经济获得发展这个“果”当成了“因”。中外历史上,凡是物质世界的繁荣,无不先有精神世界的建构:汉代的鼎盛之于百家争鸣;唐代的兴盛之于魏晋风骨;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之于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等一些列精神领域的变革。同样,当代中国社会、经济的崛起,必须先有精神的崛起。
联系到我们中国的现实,我们就会看到,当代中国经济遭遇的许多瓶颈,主要并不是没有放开人们的欲望,也不在于没有引进西方的制度,更多的在于伦理、信仰等方面的缺失,缺少一种升华、超越的精神力量。再联系到我们商学教育的现实,我们就会看到,其实学生并不缺发财致富的欲望,因为这种欲望是人本来就具有的。重要的是能否培养一种精神气质,这种精神气质才是真正做成造福社会的大事业的根本,才是作为企业家或经理人的本质。
作者常常会问家里有创业、经商背景的学生(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因地处浙江这一民营经济大省,不少学生都有家族企业的背景)一个问题:你觉得家里的事业能做起来,最主要的靠什么?同学们几乎都会提到而且强调父辈的艰苦创业的精神(无论是现实所逼还是主动出击)。有人形象地把浙商的这种精神总结为“四千精神”:千辛万苦、千山万水、千方百计、千言万语。正是基于这一点,作者在担任“创业孵化班”班主任期间,特别强调创业精神(entrepreneurship)的培养,并把创业精神阐释为“主动、坚持、责任、奉献”四种基本的精神素养,以此为班训。
而一个人精神气质的培养,必须源于我们从古至今一脉相承并不断发展、至今仍流淌在中华民族血脉中的活生生的传统。如果此一精神的培养,还要全然仰仗于外来文化的灌输,那么,我们发展出来的,就只能是一种空心的、乏力的、没有自发性和原创力的经济。
参考文献
1. 杨海锋:《儒家文化对家族企业的影响》,《科研管理》2008年S2期
2.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版
3. 涩泽荣一:《论语与算盘》,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1月版
|